天花湖水庫穿越的五座煤礦區


天花湖水庫的引水道與壩址沿線共經過 5 座已知的煤礦區,這些煤礦坑位於公館鄉與頭屋鄉交界地帶,歷史上曾長期開採,至今可能仍殘留地底坑道或疏鬆結構。
🏚️ 穿越的五座煤礦區:
1. 景山煤礦
2. 幸一煤礦
3. 興福煤礦
4. 建興煤礦
5. 大東山煤礦
這些煤礦大多位於後龍溪攔河堰至天花湖水庫之間的地段,也就是第一與第二號引水隧道的路線附近。
⚠️ 穿越煤礦區的主要風險:
1. 地層鬆動與地盤下陷
煤礦開採後可能殘留大量廢坑道與空腔,這些空間在長時間未補強或回填下會造成地層鬆動,甚至有地盤下陷風險。
當隧道施工或注水時,引發空隙塌陷可能危及隧道結構穩定。
2. 瓦斯(甲烷)累積與爆炸風險
舊煤層中仍可能有殘留甲烷氣體(俗稱煤氣),在封閉或未充分通風的隧道中可能積聚,造成爆炸或中毒風險。
即使不用炸藥開挖,若隧道通風設計不良仍有意外可能。
3. 地下水與坑道導通
老煤坑常與地下水流有連通性,一旦隧道挖掘時打通廢坑,可能造成地下水滲流、崩塌或土壤液化。
此類情況會增加滲水壓力,也可能形成隧道內部的突水現象。
4. 工程風險加劇
工程人員在施工時需面對不確定的地質條件,包括「是否有空坑、是否已坍塌、是否有瓦斯、是否已水滿」等風險,這會大幅提升施工難度與風險。
天花湖水庫地質風險揭露:引水道穿越大坑與新北寮斷層,潛藏深層危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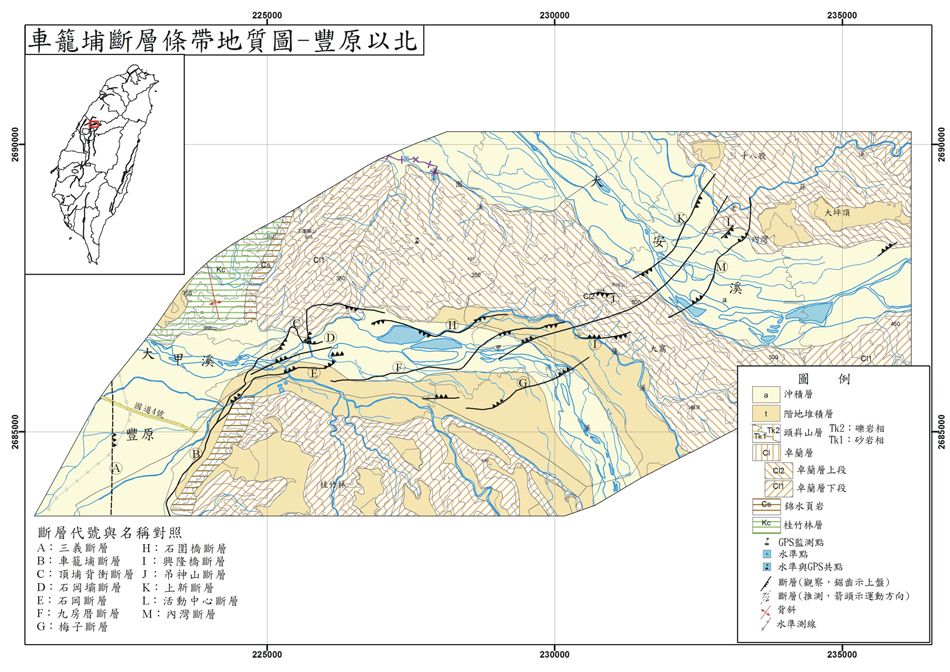
苗栗縣頭屋鄉即將興建的天花湖水庫為離槽式設計,預計透過長達9.7公里的引水道,從公館鄉打鹿坑的後龍溪上游攔河堰取水,導入飛鳳村集水區。引水系統涵蓋三條隧道、兩座跨河橋梁與一段水工設施,是一項大規模的地下輸水工程。
然而,這條引水道路線將穿越兩條具潛在活動性的地質構造──大坑斷層與新北寮斷層。這兩條斷層雖不如獅潭斷層知名,卻同樣隱藏著不容忽視的風險。
大坑斷層可能屬於逆斷層,具有地層錯動與岩體鬆動的潛在性。在地震發生時,岩層的剪裂與移動會直接威脅到隧道結構的穩定性,即使採用無炸藥的機械開挖法,也難以完全排除應力釋放導致的坍塌或結構損壞。
新北寮斷層則分布於第二號引水隧道區段,即從油車坑至北河一帶。雖然相關研究資料相對有限,但地質學界已有聲音指出該斷層具有活動性跡象,並位於地下水相當豐富的區域。在地震或強降雨條件下,不僅可能發生滲水與岩層滑動,更可能誘發土壤液化或隧道內部應力集中,導致結構受損。
引水道穿越這兩條斷層所伴隨的風險,主要包括地層破碎帶造成的坍塌、不穩岩層導致的滑動、地震引發的再錯動現象,以及地下水導通所產生的滲水或侵蝕問題。此外,這類地下工程一旦受損,其維修或補強工程往往困難重重,甚至無法即時介入,將對整體供水安全造成深遠影響。
儘管官方宣稱已採取安全施工技術與緩震設計,但在如此複雜的地質構造區,風險管理絕不可輕忽。工程安全應建立在公開透明的地質調查之上,特別是當引水道穿越多條疑似活動斷層與過去曾開採的煤礦帶時,任何潛在風險都不容模糊帶過。
在地震頻繁的台灣,興建這類大型地下水利設施,若未能充分揭示其地質結構風險,後果將難以承擔。天花湖水庫工程所面對的,不只是區域性的施工挑戰,而是潛藏於地底的結構性風險,值得社會大眾與專業單位高度關注。
獅潭斷層對天花湖水庫引水道構成的潛在威脅:斜插交會的可能性。

天花湖水庫為苗栗縣境內正在規劃中的重大水利工程,採離槽式設計,主要位於頭屋鄉飛鳳村,水源來自後龍溪上游,經由一條長達9.7公里的引水道輸送至壩體。該引水道分為三段隧道,自公館鄉起,途經多個村落後,進入頭屋鄉水庫集水區。雖然表面上工程規劃完整,但其所處地質環境卻暗藏重大風險,其中獅潭斷層的潛在影響格外值得關注。
獅潭斷層的構造特性
根據中央地質調查所的地質圖資,獅潭斷層屬於具活動性的逆斷層,具有明顯的地表破裂與構造破碎帶。更重要的是,該斷層傾角高達70至85度,並向西傾斜。這項特徵在地質評估中具有高度指標性,因為其意味著該斷層面將以極陡峭的角度從東側地表斜插入地層,朝向位於西側的引水道延伸。
平面距離不能代表真正安全
目前從地質圖可見,獅潭斷層的地表位置與引水道之間水平距離約4至5公里。然而,這樣的平面距離並不能作為「不會交會」的安全保證。由於斷層向西傾斜、角度陡峭,實際斷層面在地下的延伸可能比地表判讀來得遠。如果再考慮引水隧道掘進的深度(可能達數十至數百公尺),則極有可能與該斷層面在地下斜插交會。
更進一步指出,斷層面在地層中極少呈現整齊一致的平面,常伴隨剪裂帶、轉折面或彎曲滑動面,其走向、傾角甚至在短距離內就可能有所變異。換言之,即便主斷層線未直接通過引水道,仍有機會切入其破碎帶範圍,造成潛在的結構弱面與地震放大效應。
缺乏關鍵資料:三維斷層模型與隧道剖面深度未公開
目前水利署及相關單位並未公開足以佐證安全性的關鍵資料,包括:
獅潭斷層的三維幾何建模圖
引水隧道的詳細深度剖面與構造交會分析
斷層面與隧道最短交會距離評估
缺乏這些資訊,無法排除引水道與斷層面交會的可能,也無從確認是否落入活動斷層的影響範圍中。單以「地表距離尚有數公里」作為安全依據,顯然無法滿足現代重大工程應有的地質風險管控標準。
在未能排除這項風險前,任何貿然進行的工程都有可能埋下潛在災害的種子。天花湖水庫作為長期性水利基礎建設,更應秉持「預防勝於事後補救」的原則,審慎處理地質敏感區段。
車籠埔斷層台中 – Google 搜尋
天花湖並非是湖,也不是日本人所說的水庫

當年日本人可能並非單純以地形或水源來命名「天花湖」,而是一種帶著藝術想像的隱喻。那些由矽礦所製成的玻璃與陶瓷器皿,裝了水後,器中如湖,光影流動,波紋輕盪,宛如一泓靜水。而水面上倒映的,是器皿釉面上如花般綻放的圖紋——那便是「天花」。器如湖,湖中映花,天花湖或許正是這種工藝美感的結晶與詩意命名。
這樣的命名,也許出自日本人對自然與工藝相通的感受力,也可能是後人對礦產之美與文化記憶的再詮釋。但諷刺的是,今日我們誤把「天花湖」當作一處適合建水庫的天然湖泊,卻忽略了這名字背後可能只是藝術性、文化性的象徵。原本是詩,卻被當作工程圖解讀;原是花影水紋,卻變成沙塵漫天。
日本人才不會在天花湖蓋水庫,他們不會那麼笨!

許多人常說「日本人當年就想在這裡蓋水庫」,彷彿這是一項跨世紀的計畫遺志。但我們不妨反過來想一想:如果日本人真的想蓋,為什麼最後沒有蓋?
事實上,日治時期的工程師極其嚴謹,他們對地質、水文、集水區穩定性都有充分調查。他們一定早就看出來──這裡的山坡鬆散、上游矽礦密布、沙源驚人,一場大雨就能帶下數萬立方公尺的土石,這種地方根本不可能穩定蓄水。日本人沒蓋,不是沒機會,而是他們比我們更清楚:這裡蓋不成水庫。
因此,今天若還有人一味援引「當年日本人也看上這裡」作為天花湖水庫正當性的依據,那只能說是對歷史的一種誤解,甚至是對科學與理性的背離。
天花湖沒有花,也沒有湖,只有大量的沙:一座水庫的荒謬命名與沉重現實

這裡叫做「天花湖」,聽起來像詩一樣美,讓人聯想到山明水秀、繁花盛開的湖泊。但走進來的人會發現——這裡既沒有花,也沒有湖。真正從天上掉下來的,不是花瓣,而是數千萬噸的沙子。這些沙子每天從山上源源不絕地傾瀉而下,像下雨一樣,把整個湖面慢慢掩埋。於是,我們不如叫它「天沙湖」,這名字反而更貼近現實。
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沙子?因為這裡是露天開採矽礦的重點區域。矽砂經過簡單處理後,剩餘的沙子隨意傾倒棄置,隨著雨水流入河道,日日夜夜不曾停歇。從清朝康熙年間就有開採記錄,到了日治時期開始正式的系統化開採,至今超過三百年,造就了一條不堪回味的「沙河」,這可不是浪得虛名。
可憐的沙河,已經不是一條真正的河流。你在這裡找不到半條魚,沒有溪蛤,也沒有水草——甚至連青苔都難以生存。整條河道,像一條灰白的傷疤,靜靜躺在山谷中。沒有生命,沒有顏色,只有沙子和沉默。
在這樣的地方,竟然規劃要興建一座水庫,還取名「天花湖水庫」。試問,在一個連湖都不存在的沙河谷地,怎麼蓋出真正的水庫?哪裡有穩定的集水來源?這些沙子只要兩次颱風就能把水庫填滿,屆時不是蓄水設施,而是變成一個巨大的「攔沙池」。
最荒謬的是,這個水庫就算蓋成了,也無法提供真正乾淨的水源。大量沙子淤積會造成濁度居高不下,處理成本驚人。環境破壞、水源品質惡化、地層結構疑慮,這些問題都在專業界提出過警告,但似乎並未真正影響決策。
這樣的工程,究竟是為了解決水資源問題,還是為了滿足政治上「有建設、有經費」的目標?這樣的水庫,不是在創造未來,而是在掩埋環境與真相。
如果一定要蓋,那我們不如誠實地為它命名:「天沙湖水庫」。這個名字才真正「貼地氣」,甚至可以成為台灣水利史上的警世碑文。
天花湖水庫?

這裡叫做天花湖,其實這裡根本沒有花,也沒有湖。這裡天上掉下無數的沙子,每天都這麼掉下,把整個湖都埋掉。所以我們可以叫它天沙湖。好了,就是因為這裡是露天開採矽礦產區,所以天天都排出大量的沙子,順著河流排出來。從清朝康熙年間就開始了,所以叫做沙河。可憐的沙河裡面沒有半條魚,沒有溪蛤,也沒有水草,沒有活的生命,全部是沙子,這裡能夠蓋水庫嗎?誰相信?這裡只能夠蓋一個充滿沙子的水庫!就叫他天沙湖水庫,這個名字很美,全台第一美麗的水庫。
二十年松樹復育,歐洲做得到,我們為什麼不行?

在台灣,一談到蓋水庫,多數規劃者只想著「快點動工、趕快儲水」,卻極少有人先問:「上游的森林長好了嗎?泥沙處理有根本解決嗎?」
而在歐洲,許多國家在規劃水庫時,會等上一個世代。他們的思維不是「先蓋再補」,而是「先復育,再蓋」。他們知道,真正能決定水庫壽命的,不是壩體結構,而是上游的森林。
松樹,是一種時間的信任
松樹耐貧瘠、抓地穩、抗風耐旱,是山區礦區退化土地復育的首選。當你在一個破壞嚴重的礦區,種下松樹,就是給這塊土地一個重生的機會。
二十年後,當松樹長成林,土壤穩定了,水源涵養了,泥沙減少了,這時候才去談水庫,不僅環境安全,經濟也更划算。
但我們做得到嗎?
歐洲人為什麼辦得到?
因為他們願意等。他們把環境當作基礎建設的一部分。
德國哈茨山流域,先復育山林,再進行洪水調蓄設施;
法國羅亞爾河整治,花了30年讓河流恢復生態功能;
瑞士阿爾卑斯山地區,森林保護被納入水庫壽命設計中。
這些國家深知:不處理上游的問題,任何水庫都是沙堆裡蓋的夢。
台灣為什麼做不到?
我們不是沒有專家,不是沒有預算,而是:
政策急功近利,要「四年有成績」;
地方被短期利益綁架,要「先有水庫才會發展」;
復育工程不夠搶眼,無法剪綵、無法招商;
環境思維薄弱,森林只當作背景,而非核心。
於是,我們不敢等一棵松樹長成,就急著把水壩蓋起來。結果水庫蓋好了,沒幾年就淤滿、壩體損壞、水質惡化,最後只留下爭議與浪費。
我們需要的,不是更多水庫,而是更多耐心
也許現在,就是台灣改變的契機。
與其倉促推動水庫建設,不如先投資在山林治理、礦區復育、流域穩定。讓松樹長出來,讓土地休息,讓溪流重新呼吸。
如果我們願意等一棵松樹長成,那麼我們就會真正準備好迎接一座長壽、安全、乾淨的水庫。
歐洲人做得到,我們為什麼不行?